伊卡洛斯之翼:换血与追求永生的硅谷富豪
2025年,一部名为《长生不死:硅谷富豪的逆龄人生》的纪录片在网飞平台上线。影片以硅谷顶级富豪布莱恩·约翰逊(Bryan Johnson)的一段自白开场:“天赋,能命中他人无法命中的目标;而天才,能命中他人看不见的目标。身在21世纪初的我们该问的是:这个时代该解决的天才目标是什么?我认为是停止一切自我毁灭的行为,并攻克衰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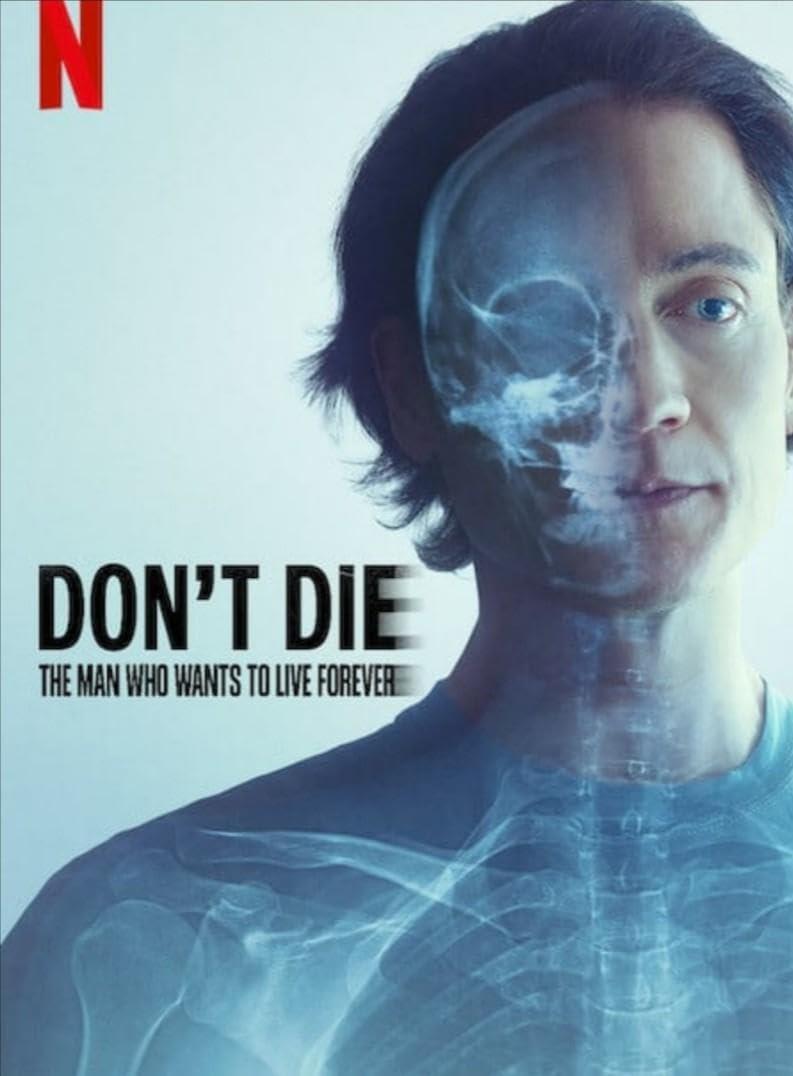
《长生不死:硅谷富豪的逆龄人生》海报
布莱恩·约翰逊立志追求永生,或探索永生的可能性。他为此不惜投入巨额财富,亲自参与各种实验。约翰逊表示自己追求永生,是因为他正逐渐迈向早逝,而他不愿接受自身的衰老、退化与死亡。约翰逊近乎虔诚地执行计划:每天服用超过130种药物加补剂;规律锻炼一小时;在早晨用电极刺激耳朵来唤醒副交感神经,使自己放松;戴上特殊耳机做听力再生训练;用高频电磁刺激腹部;戴上装有激光二极管的生发帽来促进头发生长......他甚至为自己设计了一套算法,以便更好地照顾自身健康。
约翰逊将这套计划称为“蓝图”,并公开了自己执行计划两年后的身体数据:他的身体年龄年轻了5.1岁,50项生理指标达到完美。在公开这些数据后,“蓝图”公司所推出的产品(包括补剂和橄榄油等)被抢购一空,但购买者表示其中一些产品并无特殊之处。
但是,这套计划中包含许多项激进,乃至带有极大风险的干预行为。例如约翰逊会定期注射生长激素,并试图分析其对于身体的作用,而成年人注射生长激素可能伴随导致二型糖尿病、高血糖,甚至增加患上某些癌症的风险。而约翰逊对于雷帕霉素的服用则更具争议,这种药物主要被用来抑制器官移植排异反应。根据小白鼠的实验数据,该药物能延长寿命,但风险是会抑制免疫系统,人类服用该药物可能导致严重的细菌感染。哈佛大学医学院教授Vadim N. Gladyshev 对此评论道:约翰逊对身体的某些干预行为缺乏严谨的科学依据,他的做法是非正统的科学研究方法。
在研究层面,由于约翰逊所服用的药物种类过多,研究者很难确认是哪种药物真正帮助他延缓衰老。此外,研究对象数量也局限在他一人,而能够被监管机构的研究则需要上千人的实验对象,对药物和干预的一致性要求也更为严格。也有声音认为约翰逊的做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毕竟愿意将自己作为实验小白鼠的人少之又少。
约翰逊对于逆转衰老的渴望是如此真实,以至于他在和儿子塔尔马奇一起锻炼时,由衷地羡慕儿子有力的身体,并说道:“我真想拥有他的腿。”如果说,这种表达还停留在口头层面;那么影片后半段展现的约翰逊祖孙三代的换血,则着实令人震惊。这种做法可以追溯到近年来颇受争议的血液治疗试验,给年迈的老鼠输入年轻人的血液,测试其中的活性蛋白质治疗阿尔茨海默病或帕金森症等“老年病”,帮助衰老肌体恢复活力的可能性。在硅谷,换血也被视作抵抗衰老,追求永生的技术手段。
影片中约翰逊的父亲年事已高,发现自己的头脑难以保持清醒,于是便向约翰逊求助。而后者向父亲表示,自己愿意贡献血浆,并将其称作“为挚爱的亲人所做的壮举——给出自己的一部分健康,来投资他们的健康”。之后,约翰逊询问儿子是否也愿意献出一些血浆给自己,并将这描述成一场祖孙三代的亲子活动。
事实上,血浆置换术在硅谷富豪圈子里并不新鲜:硅谷科技右翼大亨、“硅谷创投教父” 彼得·蒂尔(Peter Thiel)就被传出定期接受年轻人的血浆置换。但约翰逊是为数不多公开承认自己进行换血的硅谷富豪,他甚至在网络上被称作“第一个真正的吸血鬼”。然而在约翰逊一家看来,这次换血代表着约翰逊与曾经染上毒瘾、离开家庭的父亲的一次和解。
与极其严苛的生活作息、对永生的追求形成鲜明反差的是约翰逊与亲人之间混乱的关系。他在成长过程中经历了父母离异,他不得不省钱补贴家用;而在近乎破产边缘之际,他创立了数字支付公司,并实现财富自由;但巨大的压力也让他的家庭破碎,他与妻子离婚,离开了从小信仰的摩门教,因此与自己的母亲以及孩子们疏远。约翰逊承认自己并不擅长处理亲密关系,而在影片中他最为快乐的时刻,是与儿子塔尔马奇和好,共同生活的片段。他希望自己能通过延长生命获得更多这样的温情时刻。

《长生不死:硅谷富豪的逆龄人生》剧照
纪录片有意展现约翰逊与儿子的相处,却未能全面揭露血浆置换技术的风险,“科技早知道”播客在2023年中曾邀请到十维资本,生物医疗产业合伙人Josh Wu作出点评:血浆置换术本身带有一定的风险,包括接收者可能感染甲肝、乙肝,还要考虑到细菌、寄生虫和HIV问题。此外还可能导致接收者出现免疫抑制,过敏反应等情况。输入大量的血浆还可能带来体液过载、铁过载等问题,而这项技术的簇拥们鲜少提及这些风险。
人们对于永生的追求并不新鲜,从中获得的教训也不在少数。美国历史学家阿德里安娜·梅厄(Adrienne Mayor)曾在访谈中表示,近年来一些高科技企业正在努力追求永生不朽,而这一切早在神话故事中就有所展现。在《奥德赛》中,女神卡吕普索以永生为代价挽留尤利西斯永远待在她的岛上,而他拒绝了这一提议,重拾自我并回到妻子佩内洛普身边。黎明女神爱奥斯为她的情人提托诺斯求得了不死之身,可她却忘了永生并不等于永葆青春。提托诺斯老了,爱奥斯将他安置在一个黄金铸就的牢笼里,让他在那里日渐衰弱地走向永恒。暴君西西弗斯绑架死神桑纳托斯带来了诸多麻烦:大地上人满为患,病人痛苦而不得解脱,战争成了人类的游戏,西西弗斯因此受到桑纳托斯和诸神的严厉惩罚。
我们甚至能够发现一个不是靠神力而是靠技术(在故事里表现为药物)来寻求永生的神话:美狄亚把伊阿宋的父亲放到大锅药汤里熬煮,使他换血洗髓返老还童。后来她又把同样的技术用在她的情敌佩利亚斯身上,但是故意省略了其中一个步骤,于是给她带来的就不是青春而是死亡。
梅厄的点评也可以作为对影片开场约翰逊的一次回应:在神话中,追求永生的凡人往往表现出“傲慢”(hybris),有着“过分、出格”的样子;而英雄们的智慧和英勇则在于接受他们的有限性。
消失的未来与希望的重建
“未来怎么了?我们何时失去了它,又是什么取代了它的位置?”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史学家Trevor Jackson在《纽约书评》9月25日号上刊发的书评《如何炸毁一颗星球》(How to Blow Up a Planet)开头提出这些问题,击中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焦虑。政治科学家们发现,自二十世纪80年代初以来,关于共享一个变革性未来的愿景在全球范围内持续衰落。在各国的政党宣言、就职演说和政策文件中,关于开放未来的原则性陈述已经让位于GDP增长、减排量或遣返人数等数字目标。当弗朗西斯·福山宣告“历史的终结”时,他预见的是一个忧郁的时代——人类社会组织方式的争论已经结束,自由资本主义民主将永远胜利,但未来似乎成了一片空白,没有激情,没有斗争。
更令人不安的是,这种未来的消失并非仅仅是知识分子的哲学焦虑。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福祉经济学家Carol Graham看来,对于全球年轻人而言,它已经转化为一场前所未有的心理健康危机。她在9月5日Aeon网站刊登的《社会需要希望》(Society Needs Hope)一文中指出,曾经的U型幸福曲线(年轻人和老年人都比中年人更快乐)已经变成了线性上升趋势,这意味着18-34岁的年轻人成为了全年龄段中最不快乐的群体。在美国,“绝望死亡”从中年人蔓延到18-25岁的青年;在全球范围内,自杀率上升、焦虑抑郁增加、孤独感达到“流行病”水平。这不仅仅是个人悲剧,更反映了整整一代人对未来失去希望,暗示着人们尚未完全理解的广泛系统性失败。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史学家Trevor Jackson
Trevor Jackson认为从宏观层面看,未来的消失,首先表现为政治想象力的枯竭。正如文化批评家马克·费舍尔所诊断的“资本主义现实主义”——资本主义是唯一可行的政治经济体系,现在甚至无法想象一个连贯的替代方案。他用一个贴切的隐喻描述道:未来已经被“止赎”(foreclosed),我们被从中驱逐,现在它属于银行。
但真正耗尽未来的是气候变化。随着一个又一个目标被错过,一个又一个承诺被打破,避免全球灾难的时间已经被挥霍殆尽。《超调》(Overshoot: How the World Surrendered to Climate Breakdown,2024)一书的作者、瑞典隆德大学的两位学者Andreas Malm和Wim Carton指出,世界已经进入“超调时期”(overshoot)——官方宣布的全球变暖限制正在或已经被超越,而对此负责的统治阶级只是无奈地接受不可忍受的高温的到来。2021年,世界产生了有记录以来最大的绝对排放量激增;2022年,全球有119条石油管道、447条天然气管道、300个天然气终端、432个新煤矿和485个新煤电厂在建设中。“已经没有非灾难性的未来了,事实上它已经到来。”Andreas Malm是《如何炸毁一条管道》(How to Blow Up a Pipeline,2021)一书的作者以及同名电影的编剧之一。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福祉经济学家Carol Graham
从微观层面看,这种结构性危机直接转化为年轻人的生存困境。Carol Graham指出年轻人面临的是“对自己的未来及其获得能养家糊口工作的能力的深度不确定性”。工作性质的变化和所需技能的日益复杂、极端的政治极化和虚假信息、全球和平与合作规范的侵蚀、传统公民社会组织的衰落……这一切构成了完美风暴。
Carol Graham的研究揭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对比:秘鲁贫困青少年对教育和未来充满希望与抱负,而美国低收入青少年,特别是白人青少年,希望水平极低。更令人不安的是,美国白人低收入家长不支持孩子上大学,而少数族裔家长和社区强烈支持年轻人接受高等教育。
面对这场危机,不同的思想家和实践者提出了截然不同的未来路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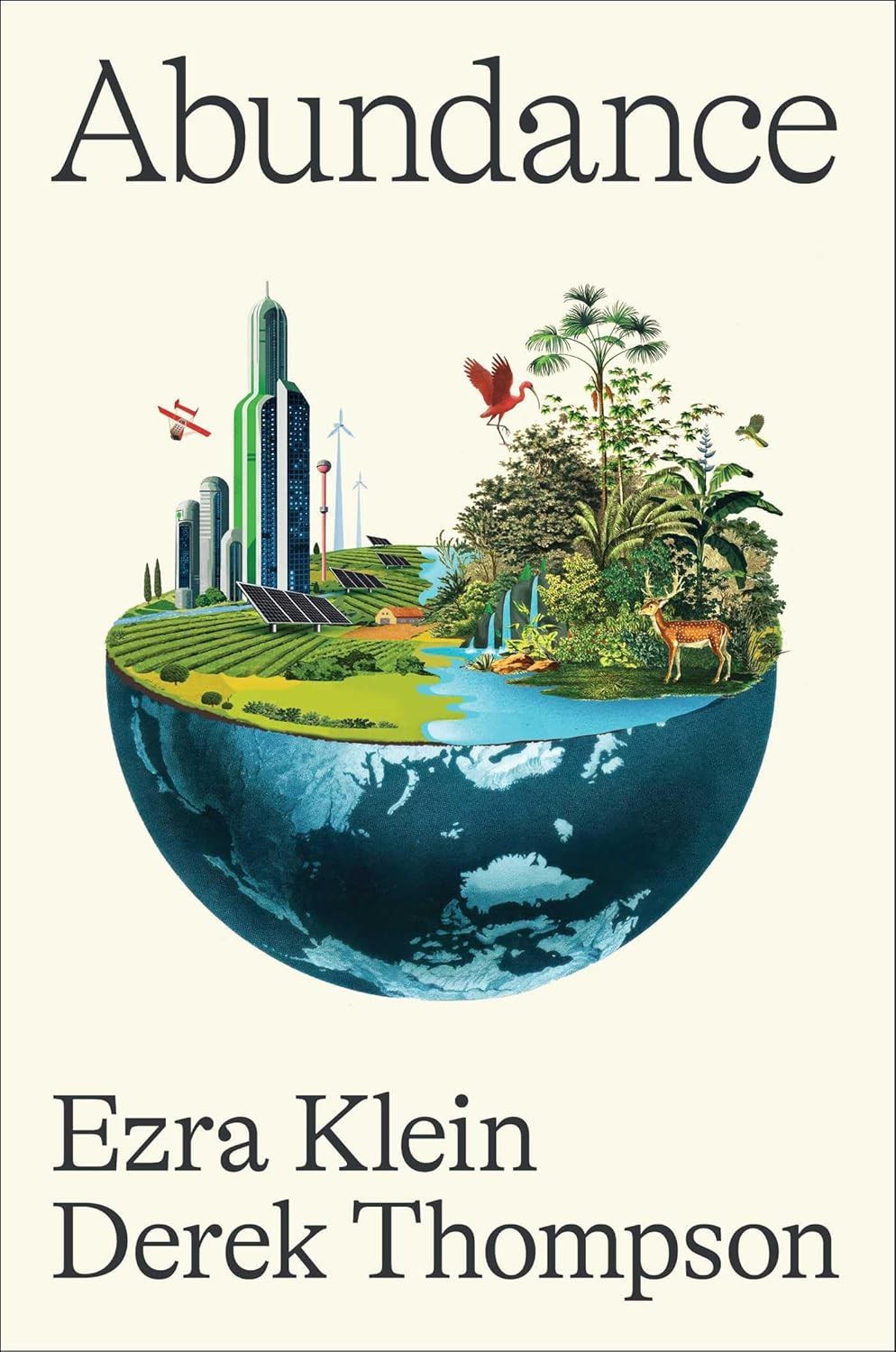
《富足》( Abundance)书封
美国记者Ezra Klein和Derek Thompson在《富足》(Abundance, 2025)一书中描绘了一个技术乐观主义的2050年:人工鸡肉和牛肉在细胞肉类设施中生长,由地热井和核电站供电;由于AI提高了生产力,大多数人几天就能完成一周的工作;更少的工作并不意味着更少的报酬,因为“AI建立在人类的集体知识之上,所以它的利润是共享的”。
他们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自二十世纪70年代以来的过度监管。自由主义变得“痴迷于程序而非结果,通过遵守规则而非实施公众意志来寻求合法性”。
他们的解决方案是去监管,释放市场和技术的力量,创造廉价而丰富的住房、能源和医疗。这是一种“建设的自由主义”(a liberalism that builds),专注于生产和增加供给,而非消费或再分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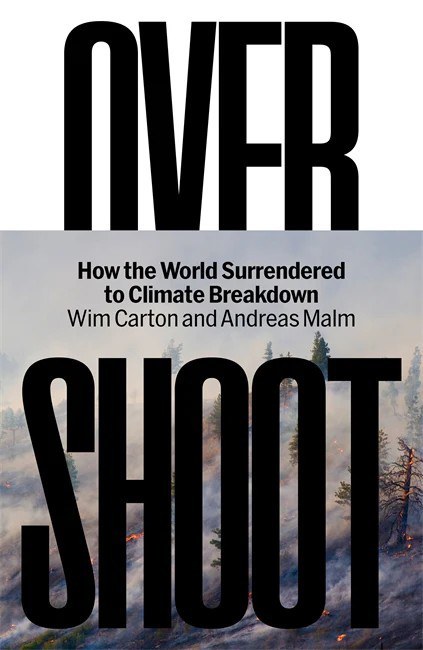
《超调》( Overshoot: How the World Surrendered to Climate Breakdown)书封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Andreas Malm和Wim Carton在《超调》中提出的革命路径。他们认为,“通往宜居星球的道路必须经过彻底摧毁一切照旧的模式”。完全停止化石燃料使用将意味着摧毁或搁浅高达13万亿美元的资本资产,这将引发普遍的金融危机、政府税收崩溃、失业、养老金蒸发等连锁反应。
但他们坚持认为这是必要的:“气候崩溃的末日规模反映在资本主义崩溃的末日规模上,如果对前者施加任何约束的话。但没有政治就不会引发这样的崩溃。”
他们设想的干预措施包括:政府取消补贴、限制出口、关闭国有土地、撤销许可、切断信贷,或直接没收资产。这虽不太可能,但却是必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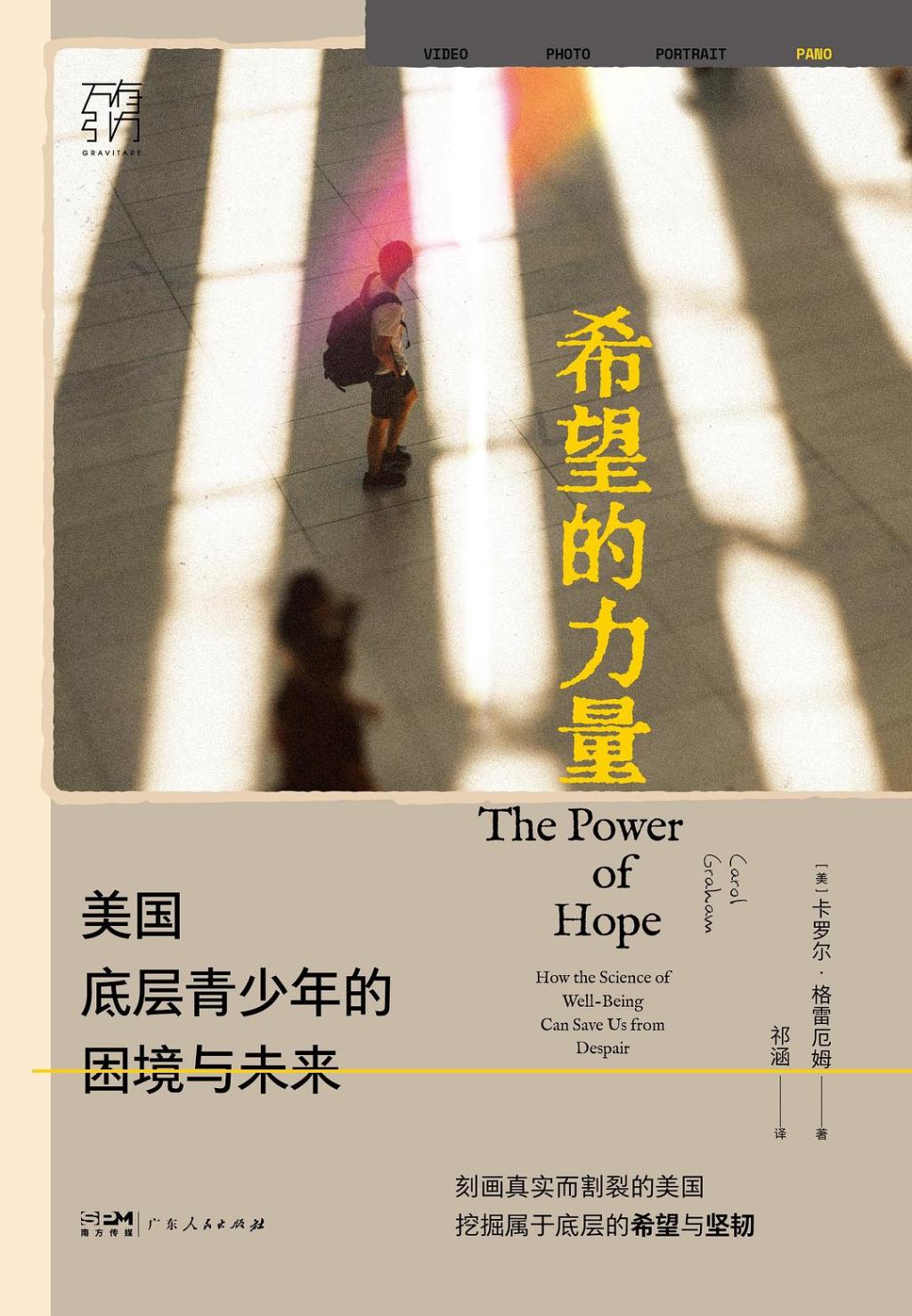
Carol Graham的著作《希望的力量》(2025)书封
Carol Graham则提供了第三条道路,聚焦于希望的恢复和教育创新。她的研究表明,希望是健康、长寿、生产力、教育成就和稳定社会关系的关键因素。希望不仅仅是相信事情会变好(那是乐观),而是相信个人有能动性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
她强调教育创新的关键作用:需要重新思考教育的提供方式,确保学生得到支持和指导。导师制度尤其重要——无论是在学校、家庭还是社区中的导师,都对指导学生做出困难决定至关重要。从芝加哥的辩论俱乐部到底特律的社区学院,从纽约的青年储蓄计划到圣路易斯的学区改革,这些成功案例都证明了一点:专注的指导可以将失败的环境转变为提供支持和灵感的凝聚社区。
尽管分歧巨大,这些不同视角确实达成了一些共识:现有体系已经失败;年轻人承受着最大的代价;需要某种根本性的变革。但在变革的主体(精英、革命者还是教育者)、规模(政策调整、系统革命还是个人赋能)和紧迫性(还有时间、已经太迟还是当下行动)上,他们存在根本分歧。
或许真相是,这些路径并非完全互斥。宏观的结构改革与微观的希望重建需要结合;短期的危机缓解与长期的系统转型需要平衡;不同层面的干预需要协同。技术创新确实可能带来新的可能性,但需要政治斗争来确保其成果的公平分配;革命性的变革或许不可避免,但也需要在个人和社区层面培育希望和能动性;教育和导师制度至关重要,但如果没有结构性改革,个人的努力可能只是杯水车薪。
Trevor Jackson在文章最后提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观察:“未来是寡头集团尚未拥有的一样东西。”( The future is one thing the oligarchy does not yet own)这句话捕捉到了我们时代的核心悖论:未来既已经被窃取、被止赎、被耗尽,又仍然是开放的、未被决定的、充满可能的。
正是在这个悖论中,我们可以找到行动的空间。民主的预期合法性正在崩溃,但这种崩溃本身也可能孕育新的可能性。气候灾难已经不可避免,但灾难的程度和我们的应对方式仍然未定。年轻人面临前所未有的心理健康危机,但正如Carol Graham从秘鲁穷人身上学到的,“在最困难的环境中,希望往往最为坚韧”。
在这个意义上,未来既已消失,又从未像现在这样迫切地需要被重新发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