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近日,第二届“澎湃·镜相”非虚构写作大赛获奖名单揭晓。本届大赛以“渺小与苍莽”为主题,特设奖金池33万元,旨在挖掘关照现实、书写时代与个体,记录磅礴与幽微的优秀佳作。大赛由澎湃新闻主办,七猫中文网、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联合主办,邀请来自学术、创作、出版、影视界的多方代表共同参与评审,从选题、信息和文本等多维度考量,最终评选出12篇极具潜力的非虚构作品,并将继续推动出版和影视改编等多种形式的内容开发。
《王玉芳》(谢东徽)获此次大赛“提名奖”,以下内容为《王玉芳》节选,“镜相”栏目独家首发,如需转载,请至“湃客工坊”微信后台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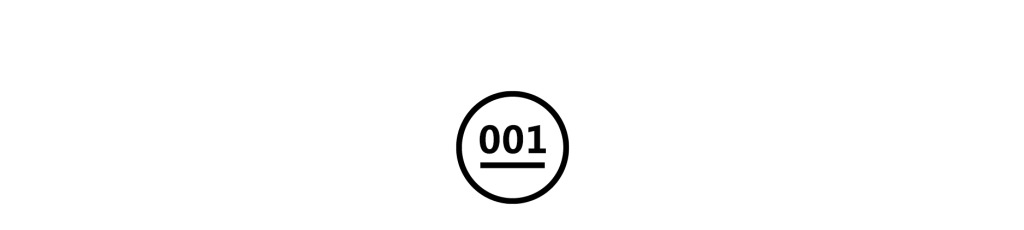
“王玉芳,我饿了!”我总跟在她屁股后头这样喊。她总会从那不足5平方的小厨房里变出各式各样的好吃的。臊子在盘子里堆成小山的手擀面,双面烤得焦黄、脆脆的烙馍,甜滋滋的油炸蜂蜜果果,薄皮大馅的大包子等。她是我从小体重就不轻的罪魁祸首,她是她很多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的奶奶、姥姥,但是对我来说,她是我最爱的王玉芳,姥爷过世以后只有我这样喊她。
我是王玉芳带大的,王玉芳有两个儿子,三个女儿,我是她二女儿的女儿。打我记事起,王玉芳便一直和她二儿子我的二舅李衡住在一起,我姥爷李有福做的是烧花盆的买卖,白银市盛产烧陶瓷的红土,王玉芳住的地方靠着大山,红土资源充足,姥爷从厂子里下岗以后就挖了两个窑洞,带着王玉芳,和二儿子,儿媳烧制花盆,日子也算是过得去。
小时候记忆最清晰的画面,进窑之前的花盆坯子一排一排的整齐码放在院子里,我就顺着中间的缝隙小心翼翼地穿过来穿过去,看王玉芳拿着毛笔在花盆上面描花,再写下花开富贵或是吉祥如意。只有小学文化的王玉芳对着老师傅的字迹描摹过上千次,行笔流畅,在无数个花盆上留下了自己的笔迹。花盆进窑开始烧了以后,就归我二舅负责了,掌握火候,把控时间。
王玉芳摘下干活的半身围裙换上做饭的长围裙,又钻进厨房,这个时候我就等着看少儿频道的大风车了,大风车播完,王玉芳就该喊我端饭了,饭菜上桌,我又出去喊守窑的二舅和姥爷,窑洞就在院子外边,离得不远,一家人就着新闻联播吃完饭,姥爷再去窑里巡查一圈,一般这个时候都会带上我,窑洞下方的碳火已经慢慢燃尽,灰烬坍缩下来,一阵风吹过,余烬闪烁出最后一丝星点明亮,便随着风升腾到空中然后消失。姥爷检查检查封堵在窑门口的棉被,堵好每一个孔洞,窑里的温度还很高,要等着温度慢慢降下来,才能开窑。检查完毕,姥爷牵着我的小手走回院子,路过门口长势喜人的沙枣树,踮脚够着摘几个树枝最顶端已经成熟的沙枣,剥了皮喂给我,沙枣很甜,姥爷看着我的笑容也很甜。二舅已经躺在沙发上看起了电视,二舅妈继续织着她女儿的毛衣。姐姐趴在里屋王玉芳的缝纫机上写作业,这个时候我是不被允许进入里屋捣乱的。跟在王玉芳身后,王玉芳洗完碗,从院子的大缸里舀出一大盆水,把我脱光放在里面,晒了一下午温热的水,瞬间包裹住我,舒服得我只打瞌睡。王玉芳笑着摸摸我的头,端出来一大盆脏衣服开始洗。打了无数个盹,姐姐写完作业也钻了进来,水温已经不热了,溢出来的水流进边上的园子里。园子里的菜秧脑袋也垂了下去,月亮爬了上来,太阳的光亮一线也看不到了。王玉芳晾好衣服,用个大毛巾被把我裹起来,抱进里屋的大炕上,挤了牙膏给姐姐拿出去,催促她抓紧上床。王玉芳在我们的洗澡水里洗洗头,洗洗脸,洗洗脚,剩下的水泼到园子里。夜已深沉,院子里静悄悄的,只有蝉鸣声从枣树和杏树上传过来。
王玉芳爬上炕给我和姐姐盖好被子,也沉沉地睡过去。
早上王玉芳醒了,我就会醒,周末姐姐上学的闹钟被王玉芳关掉了,王玉芳看着我眼珠子提溜提溜地转,拍拍我的背,示意我再睡会。在王玉芳笑盈盈的目光中,我的眼皮变重直到抬不起来。她轻手轻脚地下了床,拿上衣架上的外套,披在身上,走进了厨房。一个洋瓷大碗,卧两个荷包蛋,配上两个花卷,王玉芳端着老太太的早饭给她送过去,老太太八十四了,能吃能喝,老太太是王玉芳的婆婆,住在院子当中的小屋里,老太太早就起来了,坐在炕上趴在窗户上观察着院子里的风吹草动,听着王玉芳按掉鼓风机的开关,老太太从炕上挪下来坐在桌子边等着她的早饭,王玉芳把飘着葱花热气腾腾的荷包蛋放在桌上,老太太接过她手里的两个花卷,掰成小块泡在碗里,一边看着给她收拾房间的王玉芳,一边翻着白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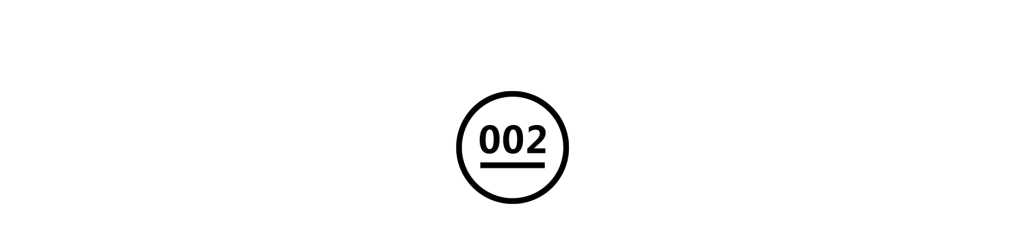
要说整个家最招人恨的,除了老太太,谁也想不起第二个人。
前几天附近死了一个老头,没病没灾的,睡着了第二天再也没醒来,享年六十六岁。老太太可一点都不像八十四岁的,早晨5点半准时醒来闹腾,家里头顶红冠最神气的两只大公鸡,每天都是被老太太的叫喊声吓得开始打鸣的。大公鸡被吓醒的时候,估计都在想,太阳还没出来,哪里来的疯婆子叫唤。
我每天早晨听到老太太在院子喊,都习惯性地用被子把头一蒙继续睡,王玉芳只得起来了。
前些年,王玉芳的儿女们挣了些钱,几家凑凑,决定修整老房子,土坯房全盖成了大红砖房,一家子一致投票通过,让老太太单独出去住,姥爷张张嘴,没出声,本来二舅打算在院墙外边单独盖一间的,结果老太太听说要被赶出住了,撒泼打滚的在家门口闹腾了三天,整的半个厂的人过来看热闹,只得同意把老太太的一间屋子盖到院子正中央。
房子盖好了,终于能松口气了,亲戚朋友来暖房后的第二天,早上五点半,老太太提着拐棍来敲门了,喊着自己饿要吃早饭,一句话就是:不得消停。
我们小孩们都不喜欢老太太,老太太恶毒的事迹,都是从二姨也就是我妈那儿听来的,也不是我妈记仇,主要还是老太太太招人恨。
老太太是我妈李雪五岁的时候回来的,她记得可清楚,因为自打那天起,家里再也没过过一天好日子,她忘不了。
老太太四十岁死了老公,也就是李有福的父亲,矿难死的,四十九岁经同村的媒婆介绍,嫁给了死了老婆五十九岁的老郑,老郑膝下无子,三个女儿都嫁人了,本来熬到了能过几天好日子和老伴享享清福的时候,没成想老伴生了一场大病,几个月就没了。老伴过世两年以后在女儿的鼓动下,又成了家,老郑老实了一辈子,也不想再娶,可是怕自己老了给女儿们添麻烦,也同意了女儿们的好意。
老太太脾气刁钻,老郑是娶了她之后才了解的,媒婆只给他看了照片,说:“这么漂亮的寡妇可不多,要娶她的男人都排着队打听呢,要不是看在你心眼好也是出了名的份上,这好事可轮不到你。”老郑心思粗,脸皮薄,哪架的住媒婆这么恭维,一来二去,答应了下来,匆匆地办了喜酒,两个人就住一起了。后面才听一个庄子的人说起,自己娶的这个寡妇刁钻刻薄在她们那儿可是出了名的。娶都娶了,钱也花了,也不想让女儿们担心,老郑一忍就是五年,六十四岁,大病一场,抱着娃她娘的照片咽了气。
老太太又搬回了儿子家。
老太太是有两个嘴脸的,在她儿子面前是一副嘴脸,细着嗓子说王玉芳,孙子孙女坏话,给儿子诉苦,把儿子身上的苦命钱压榨的一分不剩,李有福不是不清楚,只是父亲过世,母亲改嫁他心里亏欠母亲太多,他都不吭声。还没下岗前,每逢发工资,这一天不管他加班到几点,老太太都是不睡的,听到自行车的声音第一个跑出去,把儿子揣在衣服口袋还没捂热的工资装进自己缝在衣服里的内口袋,这才能睡得安稳。他的工资王玉芳是从来都没摸过的,儿子女儿们嘴馋了,攒几天的鸡蛋拿到集市上换了钱,这才买些零嘴给孩子吃。姥爷老实过了头,也从来没想着,给自己的老婆孩子偷偷藏一张绿票子红票子。
在王玉芳和孩子们面前,又是另一副嘴脸。李有福在厂上上班忙,经常住在厂子上,家里的八亩地完全靠着王玉芳一个人打理,每每都是天刚亮,她就拉着架子车出门了,生了老大李晋之后,王玉芳提前在架子车上固定好被窝,带上吃的喝的,拉着李晋在地里忙活,种小麦,种玉米,种胡麻,院子里还种花,王玉芳勤快又能干,地里院子里屋里收拾得井井有条,亮亮堂堂的。李有福厂子里的活也重,一回家,吃了饭倒头就睡,睡醒也差不多要上班了,屋里的活没沾过手。有了老二李衡,架子车上又多了一个人。李晋和李衡也在架子车上慢慢儿长大了。有了大女儿李家华以后,李衡已经3岁了,不是能乖乖等在架子车上的小人儿了,没办法,王玉芳只得把孩子锁在屋里,桌上放上吃的,孩子睡醒吃点东西,也快中午了,她再赶回来做午饭,吃完饭,挨个哄睡着了,匆匆赶到地里,太阳一落山再往回赶。好在李晋懂事,守着弟弟妹妹,除了有些磕磕碰碰的伤,也没出过啥大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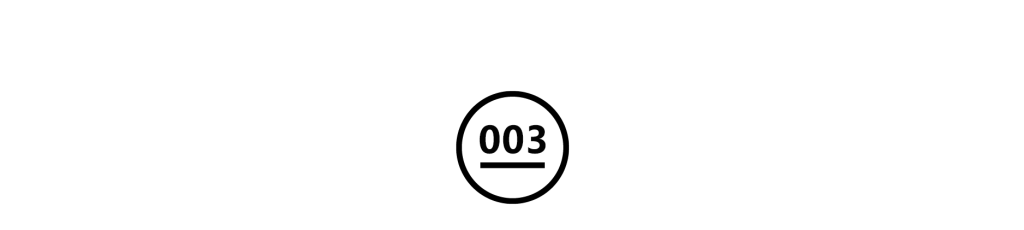
生二女儿的时候,李晋七岁上一年级了,跟着妈妈早出晚归上学,家里照顾妹妹的大哥哥变成了李衡。农忙的时候,李晋也能跟在妈妈后面帮点忙。日子除了苦点累点,也过得去。老太太回来的时候,李晋李衡都上小学了,五岁的李家华带着一岁的李雪在家,王玉芳每天下地一直是带着两个姑娘的,老太太总阴阳怪气的给李有福说,自己老了不中用了,王玉芳连孙女都不给带,加上硬挤出来的两滴眼泪,李有福说服了王玉芳,把两个小孩放在家给老太太带。
这也是李家华噩梦的开始。王玉芳一走,老太太踢开门,被子一掀,把李家华从炕上拖下来,喊着让干活。喂鸡喂猪,洗衣服,烧饭,王玉芳在家的时候,李家华哪干过这些,老太太才不管,一样一样教,学不会打会,老太太专门从柳树上剪了一根藤条,缠上一圈细细的废旧电线,打到身上钻心的疼,又不会留下太大的痕迹。李家华刚开始给母亲告状,老太太便拉着王玉芳一起打,王玉芳给李有福偷偷抱怨过几回,李有福最多说句,“咱妈那是教育小孩,谁家小孩从小没挨过打,”也就不了了之了。王玉芳心疼姑娘,却也没办法。李家华懂事,看不得母亲辛苦一天回去还要挨打,也不告状了。老太太谁都打,李衡李家华挨的打最多,李晋长得壮,藤条抽到身上没几下,人跑没影了。
有一回,李家华睡晚了,老太太醒来没吃上饭,老太太边骂边拿藤条抽,李家华一哭,两岁的李雪跟着哭,老太太怎么骂李雪哭声也不停,老太太一气之下抱起两岁的李雪头朝下塞进了院子里面储水的大水缸,水缸比六岁的李家华还要高出一个头,李家华搬不动有半缸水的水缸,急了,跪在地上抱着老太太的腿一直哭号着求饶,老太太一脚踹开,走进了屋,李家华看着水缸里一直挣扎的李雪,也不知道小小的身体里面哪来那么大的力气,她硬是把缸扳倒在了地上,李雪出来的时候脸憋得发紫,李家华使劲在背上砸了半天,才哭出声,李家华抱着李雪进了屋,把门朝里面锁上,搬了凳子,脸盆架子,能搬动的都搬到了门口顶住门,抱着李雪在床上瑟瑟发抖,怀里的李雪浑身湿透,一个劲地哭,哭到嗓子哑了,李家华给换了衣服,紧紧地抱在怀里,老太太在院子里骂了好一会,叫李家华滚出来做饭,最后见门推不开也作罢了。
傍晚王玉芳回来,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老太太恶人先告状,说李家华长大了,骂不得说不得,下午不干活把自己锁屋里睡大觉。王玉芳做了饭,伺候老太太吃上,才慢慢哄着李家华开了门。
李家华看到妈妈,憋了一下午的委屈恐惧全都变成眼泪,嘶吼着哭了半夜,才慢慢睡着,一句完整的话也没说出来。王玉芳第二天早上才知道事情的始末,她那天没去下地,抱着两个女儿,哭了一下午,李家华撞水缸的胳膊青紫,王玉芳涂了药膏,抱着两个孩子,任老太太怎么骂都没出屋,从那以后,两个孩子再也没和老太太单独待过。
老太太只对大孙子李晋的态度稍微好一点,这个好也仅限于吃的方面,每年的新麦子熟了,磨好的白面老太太都会锁在柜子里,剩下的麸皮是王玉芳和几个孩子的主食,早上上学前,老太太总会把李晋叫到她房间塞上一块白面烙的饼,老二和女孩们只有麸皮炕成的硬块块饼,老太太会叮嘱李晋快些吃上再去上学,一直盯着几个小孩从院子里出去,一旦脱离老太太的视线,几个小的就会哥哥长哥哥短的喊上,李晋一人掰一块,一起吃着往学校走。
有些啥吃的都锁在老太太上房的木柜子里,等到长毛了,她才会拿出来,拿个勺刮刮上面的霉斑,像给天大的恩赐似的分给几个小的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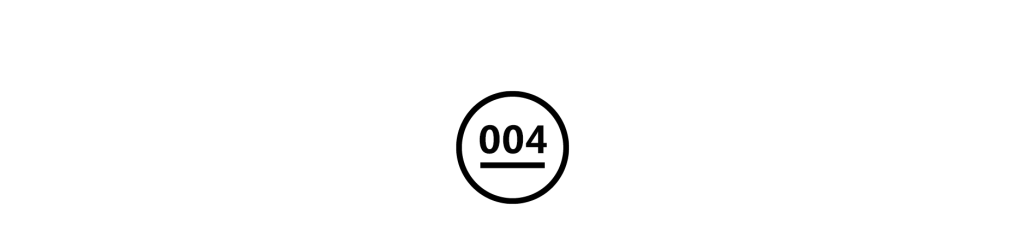
老太太最喜欢过年了,过年前两天,厂子里会给李有福发上些核桃,柿饼,这些在当时都是稀罕的食物,小孩子们也喜欢吃,李有福也知道,一旦归了母亲的手,再要出来难了,他回家之前,偷偷拿出来一小部分,包起来,埋在院子外边的枣树下面,等到晚上老太太睡着了,再偷偷跑出去,挖出来,叫醒几个孩子一起吃。这也是当时难得从老太太那里偷来的快乐。
过年小孩也是开心的,过年前一个月,李有福从老太太那儿要点钱,交给王玉芳,王玉芳拿着钱去集市上扯点当时流行样式的花布,农忙回来的晚上,缝到半夜,给四个小孩一人缝一套棉衣,纳一双棉鞋,一直放到三十那天的早上,四个小孩一睡醒,都有新衣服穿,老太太是不舍得多给一尺布的钱的,王玉芳身上穿的棉衣,棉絮都化成一疙瘩一疙瘩的,全是窟窿眼,冬天出门,风从四面八方窜进来,李有福看不过眼,骗老太太给自己扯布做衣裳,才给王玉芳做了件新棉袄。
除夕一大早,家里养的最肥的那头猪,是要被当“年猪”杀掉的,家里的猪呀、鸡呀的都是李家华和李雪喂大的,她们最爱那头头上有坨黑的花猪了,李雪给它起名叫黑妹,黑妹仿佛有灵性,李雪每回赶猪出去放猪,黑妹都会牢牢地跟着她,能听懂她说话似的,喊她慢点就慢,喊她跑快点就快,养了两年多,黑妹长得最好了,李雪怕过年要杀黑妹,过年前一个月李雪偷偷给黑妹控制饮食,黑妹还瘦了些,杀年猪的前一天晚上睡觉前,千叮咛万嘱咐,求父亲不要杀黑妹,李有福答应了。第二天一醒来,李雪听到门外面猪的惨叫声,跑出去一看,黑妹已经躺在血泊中了,老太太提着刀,看着李雪得意地笑。李雪哭着大喊杀人犯,跑了出去。
晚上李雪被两个哥哥从后山找回来,年夜饭已经上桌了,李雪哭着死活不吃饭,李有福又是给糖又是给压岁钱的哄了半天,才上桌。上桌以后,老太太故意往李雪碗里夹五花肉,还说,“猪是畜生,畜生是给人吃肉的。”李雪把碗一摔,大喊一声:“你才是畜生。”跑回了屋。
从那天起,李雪天天盼着老太太死,摔死,病死,噎死,撑死,怎么死都行,盼到结婚,出了嫁都没盼到。
老太太倒是在诅咒中,越活越精神,年纪大了,除了腿有点瘸了,啥大病都没得过,胃口比个年轻大小伙子都好。
李家第一个结婚的是李晋,十九岁的李晋,高中毕业,看着父亲在厂子里累的人不人鬼不鬼的,死活不去厂里安排的工作岗位,经人介绍,在不远的王家山煤矿找了个安全员的活,那时候时兴自由恋爱了,李晋和矿上宣传部长的女儿看对眼了,宣传部长在女儿一哭二闹三上吊的威胁下,提了一个条件,只要李晋能倒插门,不仅能娶他女儿,还能给他买房提供工作。
倒插门那时候在农村人眼里算不上奇耻大辱,但也是不光彩的事情。李晋考虑了很多天,还是不顾一家人的劝说,答应了这门婚事。结婚那会,老太太提着拐棍戳到了他的胸膛上,骂他丢李家先人的脸,打那以后,只有逢年过节,李晋才愿意回家。
隔年,李雪也找了对象,嫁到了另一个厂的片区,亲家来提亲的时候,老太太还狮子大张口,讹了一大笔钱,李雪是婚后才知道的,知道以后问父母,父母都不知道这笔钱,也不知道这笔钱的下落,李雪对老太太的恨又加深了一笔。
那一代的积怨也自然而然地延续下来,到了下一代身上。王玉芳和李有福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李雪心疼老娘,经常回来,帮王玉芳收拾收拾屋子,和老公吵架了也躲回来。李雪看小孩看的牢,只要是看到我们接近老太太,就冲上来呵斥,有时候还当故事一样的给我们几个小孩讲讲老太太的恶毒行为,慢慢儿的,老太太在小孩心里也像是喂白雪公主吃毒苹果的老巫婆一样的存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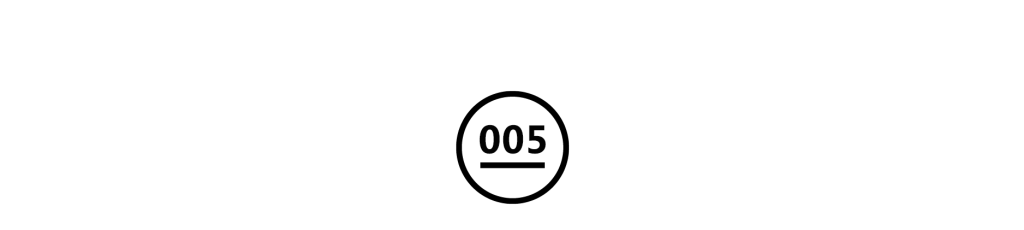
我和老太太是接触时间最长的,我有时候对我妈说的话将信将疑,老太太老得皮包骨头,脸皮层层叠叠的耷拉下来,眼睛都没见睁开过几次,怎么能有我妈说的那么坏。
家里没人的时候,我偷偷跑到老太太的窗玻璃上往里看,老太太多数时候都在睡觉,有时候开着姥爷搬到屋里的老旧黑白电视机看电视,黑白电视都是雪花,模模糊糊的看个影,爷爷说老太太眼睛不好,主要听声,有一回,我在院子里听到老太太屋里的电视机在播西游记,我趴在窗户上看,看得出神,没发现老太太出来,一转头老太太伸出手,手里有一颗花生。
我看了一眼,我妈吓唬人的表情一下跳进了脑子里,转头就跑。从那以后慢慢的,我敢偷偷进老太太的屋了。平常按时按点的,王玉芳会给老太太送饭,姥爷平时也会进去坐坐,其他人都不愿意进去。第一次进去,屋里一股陈年木头腐败的味道混合着老年人特有的气味,有点呛,老太太躺着,也不闭眼,呆呆地望着天花板,我喊她,“太太”老太太转过头来,看看我,从衣服口袋里摸出几个花生递给我。
这样的隐秘交易持续了一段时间,我对老太太的感觉有了变化,坐在老太太旁边,觉得她好可怜,人老了,是不是都这么可怜,骨瘦如柴,身上的关节像是冬天掉光叶子的枯树枝,横亘在苍茫的天地间,眼睛里也没有了水汽,像是一口再也抽不出水的枯井,一眼望到了头,再也倒影不出坐在对面的人影来。我想到了王玉芳,想到了姥爷,他们会不会也会有这样的时候。
我心软了,我忘记了我妈和我们讲的一个个都以所有小孩气愤诅咒结尾的故事,偶尔偷偷摸摸的趁着别人不注意,溜进老太太的小屋,陪她坐一会,帮她剪剪指甲。
我害怕,怕这个已经习惯了她存在的老太太,突然消失。
厂子里甭管红事白事都一样的热闹,都请一样的唢呐队,一样的做菜师傅,一样的主事人,给我一种悲喜界限不是很分明的错觉,唢呐又有一种什么气氛都能加倍渲染的力量,每当唢呐的哀调响彻厂区的上方,随之接上的是家属的痛哭哀嚎,王玉芳在厂里人缘好,总被拉去帮忙,我作为王玉芳的跟屁虫,自然也是一步不落下,王玉芳忙的时候,我就偷偷跟在一群穿着孝服吊唁的孙子孙女身后,小孩多半是没几个真哭的,真哭的也是被队伍前面走着的爸爸妈妈踹哭的,挤不出眼泪的,也得嚎,仿佛不哀嚎几声,死的人会不瞑目似的,一切流程走完过场,大家上桌吃肉,炖的十分入味的大骨头,炸的金黄流油的千刀酥,乡里乡亲的坐在一起聊聊天,美美的吃上一顿,算是送行了。
起初我是十分不理解的,怎么喜事丧事都离不开吃,喜事吃是为了分享喜悦,那丧事呢,慢慢的,从王玉芳和乡里乡亲忙碌的身影和闭口不言的神情中也懂了,吃是为了给活着的人一份慰藉,一份好好活下去的祝福。
如果唢呐声里哀悼的是老太太呢。初一下学期,傍晚放学回来,我妈让我抓紧吃几口饭,跟她去姥姥家,“我们不是前天才见的王玉芳嘛,王玉芳还给我做臊子面了”我问她。
“老太太咽气了,你爸已经过去了,我们也去。你快吃吧。”老太太走了。享年九十二岁。喜丧。唢呐队搬到了家门口,邻里街坊的都听到了动静过来帮忙,大锅大灶也搭了起来。妇女们忙着准备食材,王玉芳穿梭在院子里,又是最忙碌的那一个,看不出任何悲伤。灵堂的孙子辈们还在讨论着学校发生的事。所有人都接受了老太太悄无声息地离去。出殡的当天,王玉芳和姥爷抱着遗像走在送葬队伍最前面,大舅,二舅,大姨夫,我爸和亲戚的几个叔叔,抬着棺材跟在后面,我们这些小辈走在后面,大姨和我妈的声音最大,撕扯着嗓子叫喊着,分不清是哭声还是骂声。我只记得走了很长很长的一段路,走到后面整个人群都没有了声音,只有悲怮的唢呐声,仿佛在替队伍开路。棺材下葬的最后一刻,王玉芳才放声嚎啕大哭起来,大姨,小姨和我妈抱着哭得瘫坐在地上的王玉芳一起哭,哭得不是已经躺在地下的老太太,哭得是这么多年来自己的经历和命运。
老太太下葬以后姥爷的身体就一天不如一天了,日渐消瘦,睡不着觉,查出来是糖尿病,王玉芳又开始想着法儿的伺候姥爷,二舅又生了二闺女,三儿子,带孙子孙女的琐碎事,填满了王玉芳的日子。
李有福也就是我姥爷,一辈子不抽烟不喝酒,没有任何不良嗜好,家里穷,没吃过什么好吃的,到老了得了这么个富贵病,我妈总说老天爷不公平,抱怨自己的命运,抱怨自己娘家人的命运,王玉芳总说她,“老天爷不能乱说,给你的安排的,你就接受。心放宽,日子才好过。”
老天爷没有很偏爱王玉芳,老太太走了两年后,李有福突发脑溢血,倒在了唯一爱了一辈子的象棋桌上。出事那天,王玉芳早上起来心就突突地跳,姥爷像往常一样背着小马扎,揣着王玉芳煮的梨水,和坐在门台子上摘韭菜的王玉芳道别,王玉芳喊他早点回来吃他最爱吃的韭菜鸡蛋饺子。饺子包了一半,王玉芳就被厂里一起下棋的人叫到了医院。几个儿女也陆续到了医院。
重度脑溢血,抢救的希望不大,抢救回来也很大程度是植物人,王玉芳站在手术室门口,看着哭成一团的儿女,异常冷静,儿女一致要求抢救,花多少钱都要抢救,王玉芳却不顾阻拦在放弃手术同意书签下了名。“你爸明明白白,干干净净一辈子,到时候走了就让他安心的走吧。”
拔了氧气管的姥爷,心电图慢慢变成一条直线,放在轮椅上抬回了家。二舅去张罗丧事用的东西了,大舅去看棺材了,大姨用热水给姥爷擦拭身体,我妈哭得眼睛都睁不开,靠在沙发上,小姨在兰州上学,正在往回赶。
王玉芳从里屋拿出李有福用得褪色的毛巾,放在热水盆里淘干净。李有福得了糖尿病以后瘦了许多,王玉芳第一次发觉李有福脸上深深浅浅的皱纹已经布满了全脸,照顾眼前这个人衣食起居五十多年,第一次这么仔细的看他。日子好像一下子就过完了。
日头很烈,晒在院子晾衣绳上的竹席发出哔哔啵啵的声音,像是马上要燃起一把火,竹席弯曲的弧度越来越大,啪一声从中间折开断成了两片,掉在地上扇起一片土雾,坐在边上给苞米脱粒的王玉芳将这土灰倏然吸进嘴里,丢下手中还剩一半的苞米棒子,在围裙上擦了把手,站起身拾起离自己近的一片竹席,换了个方向搭在晾衣杆上,又去拾另一片,两片都搭好后,她走进上房拿出炕上用来扫灰的小扫帚,她皱了皱眉头,抡起扫帚打了上去,竹席两头因为受力猛然弓起来,却没有反弹回来,断裂开来,剩两根没有完全断开的竹条还连在一起,尘土飞扬。她把席子一把拽下来,进屋把李有福的衣物,盖过的被褥,李有福藏在柜子深处老太太的东西尽数抱出来丢在席子上,去厨房拿了生火的火柴,点燃了一把火。仿佛是想连同自己内心的记忆一起烧掉,很多很多想起来都不知道自己怎么能熬到今天的回忆。
(除王玉芳外,其他名字均为化名)
作者:谢东徽;编辑:吴筱慧

海报设计:王璐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