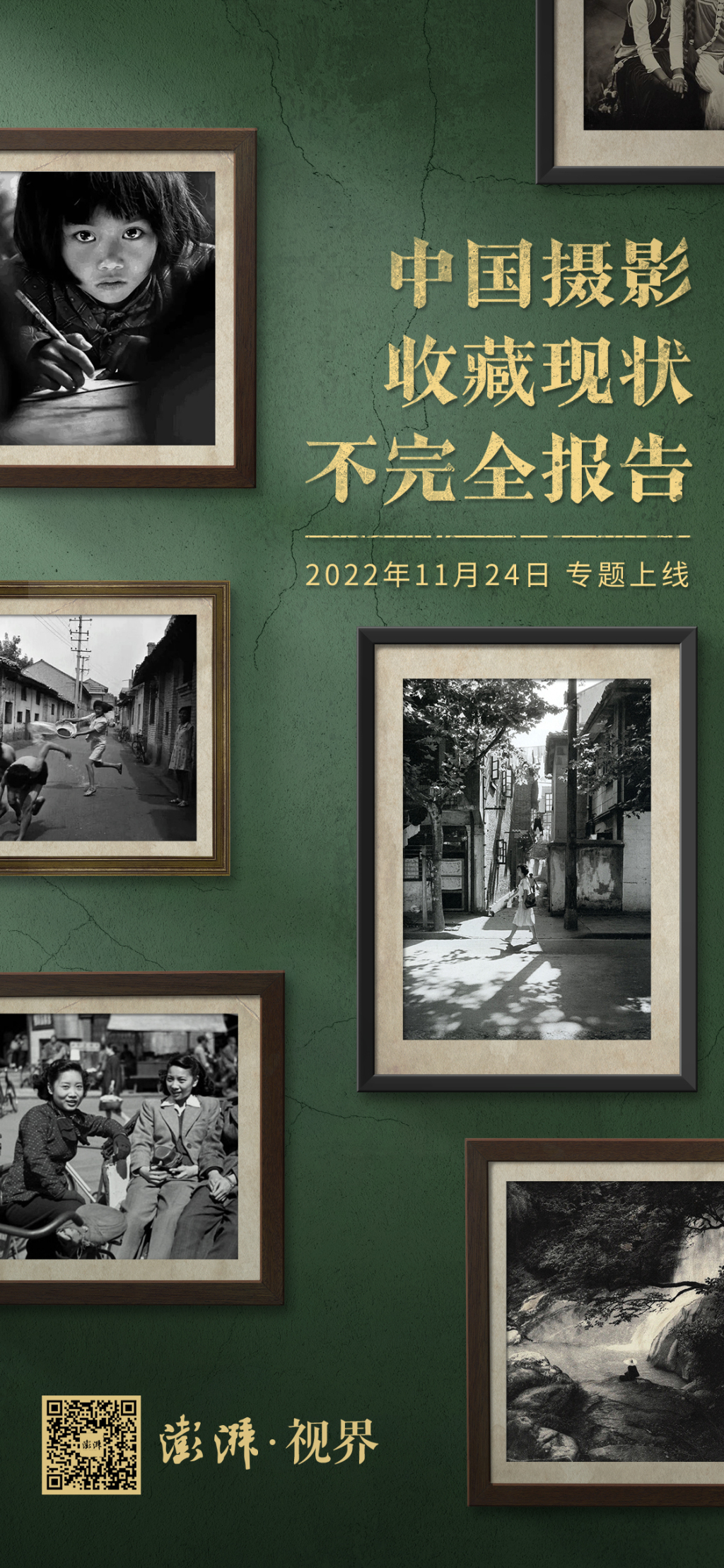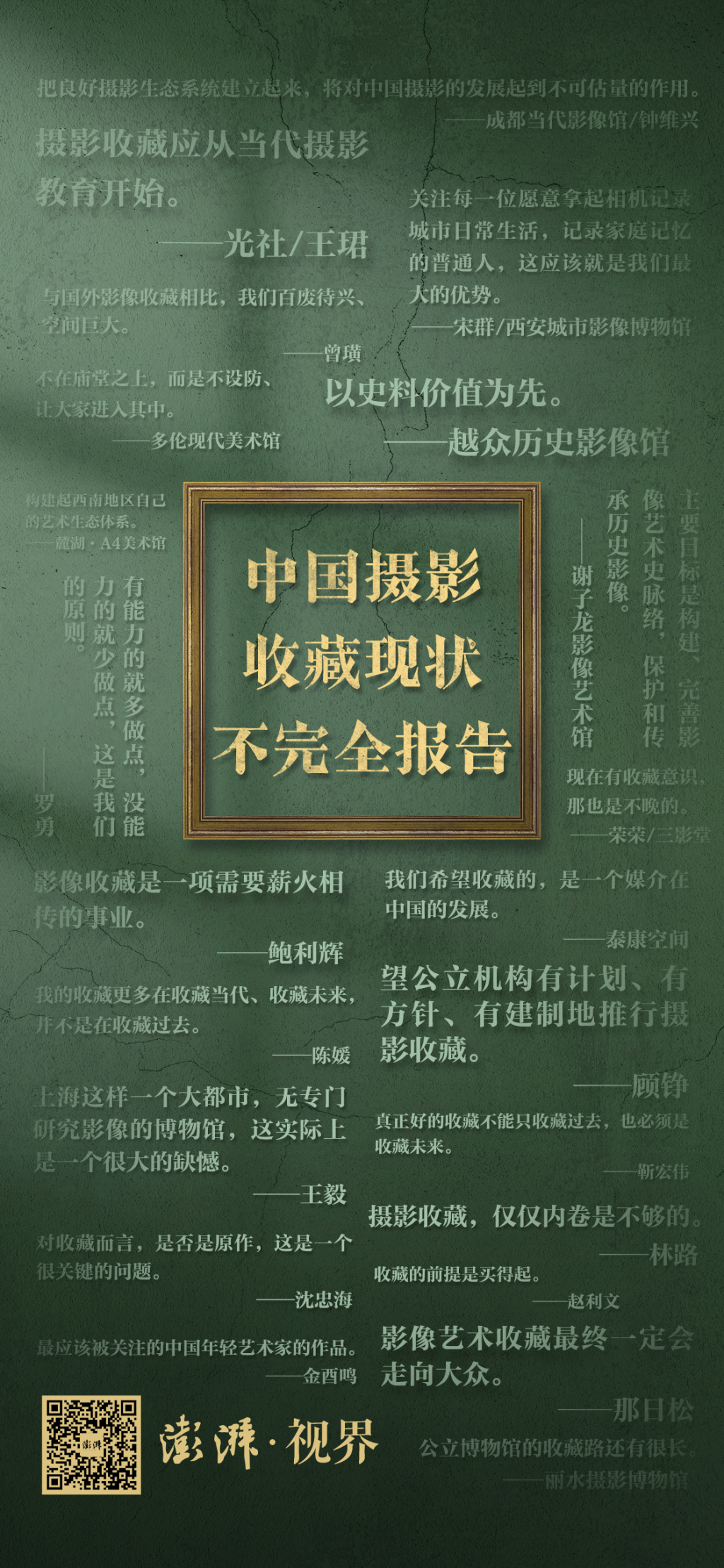
【编者按】在仅有二十多万欧元预算的情况下,一座一百万人口的欧洲城市如何撬动全城文化资源,打造出同时拥有100个展览的国际摄影节?德国科隆摄影节(Photoszene-Festival)的实践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样本。
其核心策略在于“杠杆效应”——政府以较小的资金精准投入两大项目:国际艺术家驻留计划和全球公开征集展。由此,激发了全城90余家机构自发参与,涵盖了商业画廊、美术馆、博物馆、艺术院校乃至扎根工业园区或社区的非营利空间,形成全城规模的摄影生态网络。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其“档案活化机制”。艺术家通过研究历史影像重构城市叙事,使摄影成为连接过去与当下的纽带。这种“深掘本土记忆,开放全球创作”的模式,既规避了文化过度功能化的陷阱,又巧妙平衡了专业性与大众性。
反观国内,当社交媒体将城市记忆简化为碎片化怀旧时,科隆摄影节启示我们:建立系统性影像档案库,并鼓励创作者深度介入,或许是激活城市文化基因的有效手段。国内如上海等一线城市拥有不逊于科隆的历史影像资源,如何将其转化为推动持续创作的引擎,这需要政策制定者突破“文化即旅游配套”的思维,以更开放的档案管理机制和长效扶持计划,为艺术与城市的共生提供土壤。
一座城市的摄影节的真正价值,或许在于让城市成为一本不断修写中的视觉之书。我国的摄影节热,起起伏伏,也正经历从“量变”到“质变”的关键转型时期,想要真正可持续高质量地发展下去,在于保持文化深度与大众参与之间的动态平衡。
2025年5月,独立策展人施瀚涛先生受邀前往德国科隆摄影节,以下是澎湃新闻对其的采访。

受邀参访本届科隆摄影节的7位策展人,他们来自不同国家的摄影策展人和评论家,年龄大多是70后和80后。施瀚涛代表中国参加(后排右一)。
许海峰:请介绍科隆摄影节之旅?
施瀚涛:我这次前往科隆摄影节的访问交流是经歌德学院推荐,由德国北威州文化办公室接待的。他们有一个“国际访问项目(IVP)”,经常邀请各领域的艺文工作者与北威州的各个文化艺术机构展开交流,包括科隆、杜塞尔多夫、埃森等城市,而科隆摄影节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项目。这次我们一行共有七位来自不同国家的摄影策展人和评论家,年龄大多是70后和80后。
科隆(Köln)这座城市规模不算大,一百万人口左右。摄影节的预算也有限,每届约为20万-30万欧元,无法与法国阿尔勒摄影节这种五六百万欧元以上的预算相比。通过本次访问交流,我认为其成功之处在于当地政府如何以有限资金调动全城对摄影文化的关注与支持。我了解到,这20万-30万欧元,除了日常运营之外,主要用于两个核心项目:第一项是“Artists Meet Archive”(艺术家相遇档案)。每届摄影节他们会邀请5位国际艺术家赴科隆驻留,两年间艺术家可以多次访问科隆,主办方提供住宿及少量创作经费。艺术家可深入各类拥有档案资料的机构展开调研创作。

本届“艺术家相遇档案”入选的五位艺术家。© buerofuerkunstdokumentation
例如,本届驻留项目包括香港艺术家何颖嘉在人类学和民族志类型的Rautenstrauch-Joest博物馆研究德欧殖民档案,创作了与德国在青岛殖民历史有关主题的作品。希腊艺术家Elena Efeoglou则根据“科隆摄影收藏/SK文化基金会”所收藏的奥古斯特·桑德20世纪德国人的肖像作品,借用AI手段为画面里那些近一百年前的被摄者构造出一系列既带有历史语境又充满情感的个人图文故事。还有波兰艺术家Marta Bogdanska在专门展示科隆城市历史和文化的科隆市立博物馆里驻留,她借用该博物馆内的报纸和图像档案,讲述了科隆动物园里一只曾经为几代科隆人所喜爱的具有传奇色彩的猩猩的故事,由此探究动物和人及城市的关系。另外还有两位艺术家则在著名的科隆大教堂和路德维希美术馆驻留和创作,这里不再赘述。可以说,这一驻留对创作起到了非常实在的有创造性的孵化作用。

艺术家Elena Efeoglou在现场介绍自己的作品。© buerofuerkunstdokumentation

艺术家何颖嘉在现场介绍自己的作品。© buerofuerkunstdokumentation

艺术家Marta Bogdanska在现场介绍自己的作品。© buerofuerkunstdokumentation
摄影节第二个核心项目则是基于一个主题性的全球公开征集活动而策划组织的展览。主办方每年会设定一个主题,比如本届主题为Feelings & Photography,探讨摄影和感觉/感受的关系。征集发出后共收到上千件作品,最终选出24组作品在两个不同的空间展出。这些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呈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当代摄影创作中的各种情感的表达,其内容也延伸至个人和自我、社会和家庭、文化和政治等多维复杂的层面,形式也丰富多彩。
除了上述两个核心项目之外,在5月份,科隆的文化艺术机构,包括商业画廊、美术馆、博物馆、艺术院校、非营利机构也分别推出最新的摄影展览,本届列入主办方推荐清单的就有99场摄影展。其中既有如路德维希美术馆推出的“Street Photography:Lee Friedlander、Joseph Rodreguez、Garry Winogrand”等经典摄影的回顾和研究,也有曾在去年厦门集美阿尔勒摄影节上获奖的Bruce Eesly的“新农场”系列这种借用AI手段的最新创作。除了这些展览之外,还有如科隆媒体艺术学院所组织的两天的学术研讨Another State of Mind: What We Feel, What We See, What We Do等学术论坛、艺术家讲座、工作坊等研讨和交流活动。所以,我觉得摄影节就像依靠一种杠杆效应,通过对于少数几个重点核心项目的持续坚持和精心组织,来撬动遍及全城的摄影和艺术资源,使得摄影成为该城市这一时期的焦点。当然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其背后也有这座城市、国家或地区本身的文化因素在起作用。
许海峰:就你所感兴趣的展览或者运作方式,请结合一些具体的案例?
施瀚涛:在科隆艺术工作室(Kunstwerk Koln)举办的“1890至今的科隆女性摄影家”展览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展览涵盖了从19世纪末至今的共四十三位(组)女性摄影师的作品,每位艺术家有大小不一的单幅或一组作品展示;展品多为由机构或艺术家出借的原作。展览规模不算大,但也专门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可以说为科隆的女性摄影史建立了一份索引,为未来的研究者进一步深入地工作提供了基础。这个展览以三位策展人近两年时间所做的独立研究为基础,完全依靠社会和政府的多个文化艺术类基金的支持而展开。展览所在的科隆艺术工作室其实是一片紧邻科隆国际会展中心的偏郊区的旧工业园区,园区内有超过150位艺术家在其中设立工作室,并设有一个展览空间和一个活动空间,各300平方米(这个展览就在展览空间内)。

科隆艺术工作室“1890至今的科隆女性摄影家”展览现场,策展人Wolfgang Vollmer正在导览。摄影 施瀚涛

科隆艺术工作室“1890至今的科隆女性摄影家”展览现场。摄影 施瀚涛
此外,本届摄影节的三个与摄影书相关的活动也非常有意思。一个是摄影书市集,就和国内曾经蓬勃发展的摄影书市集类似;它在市中心一个经过改造的旧纺织品商店内举办(这也是“Feelings & Photography”主题展的空间之一)。另一个是由摄影书博物馆主办的摄影样书奖,类似我国的“无像样书奖”;艺术家向主办方寄送样书,经专家学者评选后展出。它在Rautenstrauch-Joest 博物馆二层大厅举办,入选者来自世界各地,也有好几位中国艺术家入选。还有一个是科隆摄影书博物馆的展览Nobody’s Library,展出了著名英国纪实摄影家Stephen Gill从2005以来的40多本摄影书。世界上专门以摄影书为主题的博物馆大概仅此一家,但自从2014年成立以来,它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位于居民区街角的科隆摄影书博物馆外景。摄影 施瀚涛

Stephen Gill作品展在科隆摄影书博物馆的BUNKERGARTEN空间举办。图中参加开幕式的嘉宾中,73岁的资深女性独立策展人Tina Schelhorn(左一),和左右两位男士是博物馆的创办者和合伙人。摄影 施瀚涛
它坐落于居民区里的一个不起眼的街角,书展的展示空间称为BOX,面积不足100平米;但走进里面,还有一个两三百平米的办公室和图书馆,馆藏3万余册摄影书。而离BOX步行约五分钟的同一个社区里的另一个角落,还有一个博物馆所属的作品展览空间BUNKERGARTEN。它是一个废弃的花园,但主办方非常巧妙地将其改造为一个可以做半室外的展览+工作坊活动+酒吧的多功能空间,当时展出的也正是Stephen Gill的作品。
许海峰:听上去科隆城市不大,却能吸引如此多机构参与摄影节,其调动市民参与性的方式是什么?是否源于欧洲人对艺术/影像的天然亲近感?若在中国(如上海)举办,如何避免参与度低,或者一时兴起的那种?其运作模式对我们有什么的指导意义?
施瀚涛:我相信欧洲人对摄影和艺术的热情一定是它成功的重要的基础,但90多家机构的同时参与,也反映出当地社会和政府对这个活动本身的重视和努力。不过,在观察中我发现,摄影节的观众主要还是那些艺术同行、爱好者、青年学生、文化工作者,也有一小部分应该是有着一定教育背景的其他行业的人,这和上海艺术活动的观众结构是类似的。现在国内也有很多艺术节,大多是当地政府为了推动地方经济、区域开发,或者以环保、历保的名义而发起组织的,有时也会有开发商等资本的加入。因此这样的活动总希望观众越多越好,越热闹越好。其实一来这是不可能的,一个城市包含不同的社群,不可能每个人对艺术话题都感兴趣。我们不能臆想出一个男女通吃老少咸宜万人空巷全民参与的“节日”。二来,有的活动为了追求所谓的群众参与而牺牲活动的艺术性和专业性,从而让艺术家、策划人或者各个参与机构很难再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来发挥他们专业的特长,展示他们最精彩的一面。国情不同,我们国家城市发展的阶段不同,应根据各自城市特点策划更为细致地深入的活动方案,这对城市的管理者和文化制定者提出了更高要求。
就像任何其他社群的主旨一样,艺术本身是有标准的,艺术社群也有它的门槛。任何这类活动的组织首先应该保证团队的专业性和独立性,这是一切基础;如果它本身达不到一个合格的摄影节、艺术节的标准,而只是一个为其他目的服务的文化活动,那么它其实可以归在群众文艺或者群众活动中另作别论。我觉得从社会和政府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去给予这个城市不同的社群本身更多发展空间和支持培育,而不是有什么需要就拿来为我所用。如果这些社群本身成长、繁盛起来了,一座城市的文化面貌也就自然而然丰富起来了。
许海峰:能否结合中国的摄影节再展开谈一下?
施瀚涛:我觉得国内比较好的类似的活动有集美阿尔勒以及之前的连州摄影节,他们也的确获得了摄影圈内的普遍认可。尽管他们也回避不了各种环境因素的影响,但好在他们是一个对摄影本身保持那份比较纯粹的热情,有经验、有资源的专业团队,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比较自主地去展开工作。只有有了这些基础,才有可能去发现更多有趣、有意义的摄影艺术家和作品,并介绍给公众,同时也有国内外的专业机构和个人愿意参与进这样专业的合作和交流之中。
这里我倒不是说要“为艺术而艺术”,事实上,摄影的社会性是其本质特征之一。但是这个社会性是包含在摄影里面的,不是因为它具有某种利用价值而被拿去实现一种外部要求的社会性。很久以来观众的数量是衡量美术馆博物馆,或者摄影节之类的文化活动的社会效益的标准。到了今天,有了社交媒体,直接变成了流量文化。有的美术馆甚至根据展览主题安排“演员”着装打扮在展厅里游走,以吸引观众打卡,那作品和艺术的位置又在哪里呢?这是我们要的社会效应吗?这还不如说是今天这个社会的一个笑话吧。其实,如果我们把摄影这个主题本身做好了,那它所蕴含的社会效应就自然会获得体现,甚至发挥某种社会作用。但如果只是借摄影来当作工具,那又何必是摄影呢?
许海峰:就你的观察,欧洲对东方、中国当代艺术或艺术家了解程度如何?
施瀚涛:其实这次访问我有一个有趣的发现,那就是和我同行的另外几位欧洲中青年一代的策展人,他们对中国摄影非常陌生,我们很难在这方面找到共同话题。但是我遇到的两位前辈策展人却对中国摄影有很多了解,并且也很有兴趣。其中一位是摄影论坛中心(FORUM FÜR FOTOGRAFIE)的创始人、策展人Norbert Moos(也是2006-2012科隆摄影节的总监)。当他得知我来自中国时,很开心,立即拿出他在2012年策划的展览“建筑摄影-中国制造 , 科隆应用艺术美术馆国际摄影邀请展”的画册,要送给我。这个展览有13位中国摄影家和10位德国艺术家共同参与,包含了罗永进、鸟头、杨振中、刘真辰、蒋鹏奕,以及Michael Wolf, Candida Höfer, NadavKander等。他热情地问起我这些中国艺术家的现状,并让我之后也能给他提供一些关于中国摄影的信息。而在摄影书博物馆展览的开幕式上,我遇到了已经73岁的资深女性独立策展人Tina Schelhorn(1990-1996年科隆摄影节的策划人)。她一提到中国也很兴奋,说她曾和王庆松等中国的摄影家有过长期联系,还曾助力他们的作品在欧洲展示。说实话,从不同时代的德国策展人对中国摄影不同的了解程度中,有很多方面颇为耐人寻味。
许海峰:另外一个问题,在我们的印象中,欧洲观众似乎总是有足够多的时间去观展,他们不需要工作吗?科隆的经济支柱是什么?
施瀚涛:确实,我发现下午 4 点半 5 点左右,很多科隆人就都走上街头,在小酒馆、小饭店沿街坐着,吃饭、喝酒、聊天,有的地方也有户外的乐器或者唱歌表演。后来经过询问我了解到,科隆人大多数8 点上班,下午四五点下班,很少加班。而且那里天黑得晚,很多博物馆美术馆关门也晚,晚上还有音乐厅剧院和独立电影放映等很多活动。反正就是我们前一阵常提到的那个词:松弛感。

人群聚集在Photo Pavillion外,当晚是摄影节的开幕式。该空间由科隆的一家纺织品商店改造而成,是摄影节的主展场之一。展出了包括Feelings & Photography主题展,以及Thousand Folds摄影书集市。© buerofuerkunstdokumentation
这里简单讲一下这座城市的历史背景。科隆市位于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横跨莱茵河两岸,是德国西部历史文化名城和重工业城市,也是德国的第四大城市。科隆不仅有超过两千年的历史,世界上第一台内燃机也在这里发明,马克思与恩格斯曾在此创办了《新莱茵报》。科隆在近代成为重要的展会城市,Photokina是科隆国际展览公司主办的,曾经是全世界上最重要的影像器材博览会;每两年一届,1950年创立至2018年最后一次,共举办34届。而科隆摄影节也正是在1984年依托于Photokina的平台创办的,2018年博览会停办后,2019年开始摄影节完全由科隆市和北威州政府接手主办。另外,旅游当然也是科隆经济的支柱产业。
许海峰:旅游是科隆的重要产业,科隆摄影节如何平衡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是否考虑此因素?
施瀚涛:我的观察,我所见到的艺术展览并未刻意迎合游客,如果说摄影节有一个核心的需要服务的对象,那它应该就是摄影本身,或者艺术家和作品。但是我相信好的艺术家和作品总会有它的观众,并在观众中获得共鸣,哪怕是来自远方的游客。尤其是“艺术家相遇档案”项目,这些基于历史照片和文献的在地创作,总会涉及历史和本地社会的一些话题,从而更显得生动和有趣。
例如,Bogdanska在科隆市立博物馆里驻留所关注的那只猩猩Petermann就和科隆市民的记忆有着密切联系。1947年幼年的Petermann和妈妈一起被从非洲带到欧洲,但是妈妈很快就去世了,Petermann是园长和他的女儿用奶瓶喂大的。由于精心照料和刻意训练,他从小就习惯了在床上睡觉,能在桌边用刀叉吃饭,还会表演各种节目,成了动物园的招牌。随着他年龄的增长,以及动物表演逐渐受到质疑,他逐渐为人遗忘。但在1985年的一次管理员的疏忽,让他和他的伴侣Susi一起逃出了笼子,并表现出了攻击性,甚至咬伤了园长的头部和面部。最后在“追捕”过程中,他们俩在两个不同的地方被击毙。但这让它再次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和追捧,一支摇滚乐队和足球队都用了他的名字来命名,他的名字还出现在很多街头涂鸦上,成了一个为自由而战斗的英雄。艺术家通过历史图片和新闻故事,结合自己创作的视频作品,在讲述他的传奇故事的同时,让人们重新思考人和动物及城市的关系。像这样的作品对于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来说,一定都会抱有很大兴趣。而这件作品也让人们对科隆的历史获得更深入地了解。
许海峰:他们在摄影领域的经验有什么可值得我们借鉴的吗?
施瀚涛:一下子看到这么多不同主题和形式的摄影实践,说实话我也挺兴奋的,也让我进一步坚信摄影作为一种创作媒介的无限的可能性。还是以“艺术家相遇档案”为例,它巧妙地融合了摄影媒介与城市文化——城市的历史记忆与文化精髓往往凝聚于图像档案之中。无论参与的艺术家来自波兰、中国香港或其他地区,他们的创作都必然与当地发生深刻的关联。这类项目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它邀请观众和艺术家重新审视自己城市的历史;另一方面,它也为年轻艺术家提供了示范,即如何围绕具体的历史议题进行扎实创作,而非停留于抽象的概念表达。要实现这类项目,也是对城市管理者或文化政策制定者的挑战,其一,我们需要系统性地积累和整理更丰富的档案资料,特别是图像档案;其二是建立有效的开放机制,让不同背景的艺术家能够便捷地接触和利用这些资源,当然也包括公众可以方便地接触到。
许海峰:你还有什么想告诉读者的吗?
施瀚涛:如果把视线转回上海,我们这座城市拥有海量的历史图像资源,公众对其关注度也在日益提升。然而,目前社交媒体(如小红书)上传播的内容,大多停留在浅层的怀旧甚至猎奇的层面。我们固然应该承认这种情感的个人价值,但更需思考如何引导公众进行深度挖掘,将这些图像真正与城市的历史脉络和文化身份联系起来。
许海峰:对了,听你聊了很多摄影节的东西,让我们回到我们栏目“摄影收藏”上,我们知道摄影是非常接近日常生活的一种艺术创作方式,在摄影节现场,你有注意到当地摄影收藏是怎样的情形?
施瀚涛:这次参观交流并没有安排和艺术收藏直接有关的内容,我也并没有去了解一些画廊的销售情况。但是正如你所说的,摄影是一种非常接近日常生活的艺术创作方式,所以,摄影的收藏其实好像的确具有和传统艺术收藏不同的面向。一般我们说的艺术收藏的行为,都是出于艺术欣赏的需要、艺术史的线索,甚至艺术品投资的目的。但摄影又不仅仅是传统的艺术作品,他本身的纪实性、文献性、索引性,让它同时也是关于时间和历史的一种材料。而且,它在同样保有艺术家和欣赏者的个人趣味和价值取向的同时,似乎带着更强的公共性,或者说具有更强的社会意义。

科隆摄影收藏/SK文化基金会的库房。© Die Photographische Sammlung/SK Stiftung Kultur, Köln
我想这也是“艺术家相遇档案”这种项目的意义,以及目前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开始以老照片、老相册、旧档案为基础展开创作的原因。因为这种创作可以让艺术家更直接地将自己的感受和表达与时代和社会联系起来,更直接地实现某种社会介入和批判的可能。而也正是因为摄影的这种社会性,因此它的收藏也就不仅在藏家的卧室或客厅里,或者美术馆的展厅或库房里。其实任何一个公共机构,家庭、个人,都有可能建立起它的图像资料档案;而对于公共机构来说,他们尤其有责任将自己的历史做足够和恰当地保存。而艺术家的创作则是通过介入这些资料和藏品,去不断激活并审视历史和社会(其中包括了个体和自我),从而实现对自身的再三反思和重新认识。我想这是传统艺术收藏中所没有,或者至少没有这么强烈的一个面向和意义。
所以,从这个意义而言,科隆的摄影收藏可谓蔚为大观,它庞大而细微,因为它是由这个城市的各个部门、团体和个人的多年积累、并且还在不断发展的“收藏”所汇聚而成的关于这个城市的知识和精神面貌的宝库,它也开放着等待后人以各自的方式去重访和讲述。